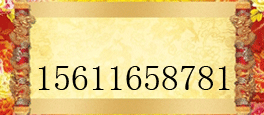王淑萍:柴灶肉香入梦来
来源:中国煤炭新闻网 发布时间:2014-04-29 09:07:22
癸巳年末,银蛇卷尾意在潜逃,群马踏春的蹄声隐隐可闻。按照习俗,家里该陆续准备臊子、丸子、肉片之类的东西了,可担心被市场里瘦肉精、激素饲料穿肠而过的猪肉防不慎防地也穿肠一次,又心悸不宁,所以寻到农户家米糠喂养的猪肉就得周折一番。
先是打电话拜托朋友,朋友又辗转到乡下亲戚家,总算帮着我落实了,才如释重负得轻松起来。
猪大腿在案板上,膘皮肉色粉嘟嘟的,确实不错。挽起衣袖,刀斧齐上,等卸成条条块块地洗了扔进锅里,看见儿子歪着脑袋站在旁边寻热闹的样子,我便自诩地说道:小时候我怎么怎么的…..儿子鱼嘴圆张,眼睛扑闪,一脸的新奇、羡慕表情。
的确,尽管时光以万夫不挡之势扭头向东而不再折返,但当我用记忆去打开我在儿少时用快乐串接的生活画面时,心域里就会漾起如同过年穿上碎花新衣般的幸福,而这种幸福不觉然地已成为我压箱底的财富,随便扯出一件就足以让儿子瞠目,唏嘘。
旧时年景
五谷不兴,灶门不旺的年代,弥漫贫苦的味道。
我们村巴掌大的版图上,伛背躬身的人们一边劳作,一边瑟缩在寒怆的时代背景下,承受着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困顿与煎熬。能够顿顿在饭桌前美美地捧上一碗稠饭,香香地打上串串饱嗝,成了他们最单纯,最真切的愿望。
三六九月的平常日子里,村里人家常常吃酱豆泡黄米馓饭,还有用黑面、杂面混和擀成的面条,或者拿铁锅焖煮洋芋和红薯干用于垫补饿肠瘦胃,不多的几撮雪花白面只能等到有重要亲友到家或遇到年节,才能舍得拿出来做了饭吃。即便如此,倘不能精打细算,还是会面临捉襟见肘、难以为继的境况。
当北风猎猎吹起,几场雪花肃然飘落,寒光和冷白统领着季节走向岁末。顺遂传统而来的“年”就像一树硕大艳丽的红梅,在中国大地上摇曳绽放起来,给栖居在农村这方角落的人们的眼里和心头,招摇起小小的欢愉和热情。他们抬头望“年”并在心里酝酿着美好的情愫:有布有面有油有肉过个好年!
可是,低头环顾家门里外,飘进飘出的依旧是习习寒凉和由此衍生的淡淡愁绪。因为愁眼、愁容、愁心都凝着“穷”字,所以“穷”在悄然间倒像根无形的红绳将村里人的情感紧系在一起。面对三两步之遥的“年”关,房前屋后的邻居人家相互接济,这家打发孩子去隔壁借三碗白面,那家女人来这家要两缸缸米,小年二十三,再给灶王爷磕个响头,上根高香(用柴棍当香),就能吃上漂着油花的年夜饭。冷清之中又透着暖意。
在我家,从我记事起,妈妈的眼睛总时不时地盯看面袋子的胖瘦。她扣扣掐掐,藏藏掖掖,家里的油盐酱醋米面粮,廊檐水似的嘀嗒着,倒也能凑合挨到过年,当然逢到短窄之处,妈妈也会使唤我去杨妈家、张妈家筹借。
最难以忘记的是在一个不寻常的腊月,爸爸凭着为生产队做架子车的木匠手艺,给二姨夫的朋友做了四个木凳,而姨夫的那位朋友又恰是城里饲养场的工人。所以年跟前,爸爸欣喜着从饲养场提回来一副猪下水,妈妈劲头十足地拾掇干净,那一年我家的年味终于香飘满院了。而这意外的阔气,却惹得弟弟有好几天肚子憋得哼哼叫,也不愿意上厕所,他是多么不舍得让吃进去的肉再出去呀!
那之后的好几次过年,我家就有了两幅猪下水,或者一副猪下水再加一个猪头这样流油的年。再后来姑姑姨姨这些亲戚家有零星养得起猪的,逢到那树红梅招展时,自己身上肉似的忍痛割上一溜肋条送给我家,让我们殷实一番“年”景,当然这也全仗着爸爸平时对他们有所付出。
年就是年,人们被轻愁和淡欢陪伴着,捧出心底所有的赤诚认真对待。
我家养猪了
旧“年”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又一道春风带着季节和政策变暖的消息轻轻拂来,三月的田野上,苦菜花开了,有了颜色。
村子里头脑活泛的人,搭鸡窝盖猪圈,抓猪娃养小鸡,精神抖擞起来,妈妈被养猪的心念迫使着,从邻村的姨奶奶家捉回来一头小猪,算是进入了村里养猪人的行列。
猪在圈里了,看着它扒墙拱地地闹腾,听着它“哧哧哼哼”地整日叫,妈妈心里不仅踏实,甚至还有些骄傲。凭着身后的一头猪,满盆满锅的油和肉仿佛就在眼前。
然而,日子是道长流水,噙在嘴巴里的感觉虽然没有以前那么苦涩了,但是贫寒的底味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,人们脸上的瘦皮尚未紧巴之前,哪里有更多的米面细粮来喂养一头牲畜,所以猪的日子就和人的日子一样清寡。那时,我每天放学后的头道任务便是提上篮子,去园子里,去水渠边给猪铲野菜,拔嫩草,或者到地头捡拾菜秧菜帮。回家后再略微剁碎,搅和上一把米糠或麦麸子倒进猪槽。但是,即便每天拔回家的菜菜草草堆成小山似的,终究还是青汁绿液,根本难以满足猪的肚仓,饿极了的猪就撞击着圈门整人似地嗷叫,所以我常常听妈妈对邻居说:我家“吊搭”着一头猪呢!吃不饱,就得和人一样吊着胃口吧。
长长的一年下来了,猪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些黏糊,情味就变得浓重起来。腊月开始,妈妈更勤地进到猪圈,瘦瘦长长的条子猪仿佛通着人性,嘴巴使劲拱着蹭着她的鞋底,喉咙里还“哼哼”地像是在告叨。妈妈摩挲着猪脖子上硬硬的短鬃、刀棱似的脊梁,再拍拍那松垮的猪肚皮,神情显得有些凝重,眼里也沁满怜惜。这般瘦骨嶙峋的身胚怎么能经受住宰杀呢?这样的柴猪怎么能让“年”油汪汪呢?
为了让猪圆实肥胖一些,妈妈咬牙将家里人吃的玉米面,黑面慷慨地献出来,接连着半个多月精面细料的用心喂养。临时磨刀亮三分,那猪的身子竟有些稍微得茁壮了,妈妈这才带着笑意,赶紧去约说杀猪的日子。
舅爷是屠夫
村里有四十来户人家,唯一的屠夫碰巧是我舅爷。
舅爷个头矮小,双腿向内罗圈,却能疾跑快走。在他黑幽幽的脸膛上,眉窝子时常拧成深旋,隐现一种肃杀之气。此外,他的嘴唇微微凸撅,话语极为廖少。或许正是这样的面相和神情,决定了舅爷的职业和猪联系在一起。
舅爷的家距离我家有百米至多,我上初中时,舅爷开始操刀杀猪,可能带着天性吧,舅爷杀猪有两把刷子,所以平时都有邻村操办红白事情的人家寻来,让舅爷一展身手。当时给人杀一头猪,舅爷可以挣到10---20块钱,还能落一条人家酬谢的猪尾巴。逢到年节,尤其是腊八已过,舅爷更变成村里的大匠人,凡有养猪的人家都赶着、牵着、拉着猪约请舅爷,舅爷也是磨刀霍霍,卷袖而上。
天气晴好的那天,爸爸叫来姑父准备将猪押到舅爷家去宰杀。爸爸打开圈门走进去时,那猪似乎已经感知到了它的大限来临,惊恐地躲在角落,端挺着耳朵细听四周的响动,更以钻心的嘶叫声抗拒着侵入。其实,在那几天里,村里已经不断有人将猪交付给了舅爷的屠刀。猪的嚎叫声从舅爷家的方向传出,震慑的不止是人的耳朵和心里,更有猪的同类同族。爸爸两步跨到猪的跟前,牢牢抓住猪的一只耳朵往外拽,无助的猪尖叫着两只前腿死死地抵住地面,姑父手里的柳条朝着猪的身上挥下去。
最终,惊魂不定的猪还是被绑在了架子车上。我和弟弟围在旁边,骇然若傻瓜蛋子似地看着,颤颤的心里多少也生出了些可怜,但是不消半刻,我们就蹦蹦跳跳地跟着架子车,护送般地朝向舅爷家。
惊天动地的时刻来临。歇斯底里的嚎叫声划破村子上空的凝冷,我家的猪被大人们死死地按压在木案子上,舅爷手中的短刀朝向了猪脖子下方,恐惧像一块黑布蒙住了我的心脏和眼帘。当我稍后怯怯地睁开眼时,殷红的猪血正汩汩地流向爸爸端着的面盆里,案子上躺着的猪声息全无,抽搐了几下就气血散尽,魂魄成殇。
舅爷的面目不带表情,短刀尖刃明晃一闪,猪的脚腕上便豁开一个口子。随即他俯下身子,嘴巴对着豁口,猛猛几下吹气,那猪的全身就像扁气球一样膨胀起来。这时候,大大的椭圆形的木盆里,才倒入的沸水蒸汽升腾。气鼓鼓的猪被抬放进去,翻转淹烫几下,软软的猪毛就被舅爷利利索索拔净。
接着,就像刚刚出浴一般,白胖胖的猪身子又被铁钩吊挂在木杆上。舅爷哗啦两瓢净水泼上,卷刃刮刀上下嚓嚓几声,细毛污渍哪敢停留。短刀再起,如剥葱脱衣一般,竖在我眼前的精身白肉便膛破肚开了,里面的曲曲折折暴露出来。舅爷双手深入其中,呼哧呼哧一顿掏挖,接着就听见他喊叫:脸盆子拿过来,快拿脸盆子!爸爸递过去脸盆,那些油油串串,肠肠肚肚之类的都被掬出来放置在盆子里。
就在我扑闪着眼睛看得热乎乎时,“噗嗤”一声,舅爷扔过来一团东西,“猪尿泡给你玩,你这个女子长得心疼”说话的同时,他瞅瞅我,嘴角咧咧着笑了,臊得我不好意地转过了头。
架子车载着白生生的猪肉,又在我和弟弟蹦蹦跳跳的护送下,颤颤悠悠地被推回家中。妈妈迎上来的目光带着喜悦和湿气,她已经劈好了一堆柴棒,锅里又烧上了热水。
柴灶肉香
白花花的肉就在锅台上、案板上,足足有八十斤啊!全家人的眉梢上像是都贴上了一个“喜”字,早早地将“年”接进了家门。
我和弟弟抢着抱柴、烧火,炉膛里红艳艳的火苗扑闪起来,大铁锅的水很快翻滚,妈妈将脸盆里的生猪血倒进锅里,慢慢的那些半凝固的血就紧紧地结成了大血块。妈妈说这样的血块,经过热油再炒一番别有风味。
爸爸的好脾气很难得地带动着他轻快的脚步,他耳朵软软地听从妈妈的调遣,将菜刀按在水缸边沿,“噌噌”几下磨得锃亮。接着一番技术性的切切剁剁,除了腿骨,排骨和留作丸子的花肉外,其他整块的肉都变成了小块。
一家人莺啼鸟啭似的说说笑笑,妈妈已将生的板油、水油切成小块,放入铁锅中炼制。在小火的加工下,这些油块渐渐变得金黄并且漂浮起来,等到不断有碎渣喷溅出来时,妈妈手持漏勺将这些渣粒捞出了锅。油香四溢,我和弟弟直接上手去抓吃那些油渣,都是为了将各自身体里蛰伏一年的馋虫喂饱。在那些年月里,这种油渣由于炸干了水分,随意放置许久都不生坏,所以就成了我家包饺子用的金贵馅料。
猪油炼好了,黄亮亮的装了半盆,妈妈说话的嗓子眼听起来润润的,像喝了蜜又像喝了油。铁锅里留着底油,妈妈将爸爸切好的生肉臊子倒了进去,又撒放调料、倒入酱油,不断地搅动翻炒。在艳艳的酱色之上,锅里水泡气泡小花似的开了败了,浓郁的肉香溢出来,盈满了厨房,又飘出屋外。此时,整个村庄已渐渐地没入寂静冷穆之中,几声犬叫从夜色的深浅处传来。投进灶膛里的劈柴跳动着火花,还伸吐着鲜红的小舌,我们一家人沉浸在热言暖语和肉香中,毫无疲惫和睡意。
第二天的时候,妈妈接着炸了丸子、酥肉,还煮好了下水,至于猪头和猪蹄呢,妈妈说要在房梁上挂几天,到了年三十的前一天,才拿下来放在大铁锅中烹煮。
做完这些的时候,距离过年还有七八天。 能源网 http://www.aeenets.com/
先是打电话拜托朋友,朋友又辗转到乡下亲戚家,总算帮着我落实了,才如释重负得轻松起来。
猪大腿在案板上,膘皮肉色粉嘟嘟的,确实不错。挽起衣袖,刀斧齐上,等卸成条条块块地洗了扔进锅里,看见儿子歪着脑袋站在旁边寻热闹的样子,我便自诩地说道:小时候我怎么怎么的…..儿子鱼嘴圆张,眼睛扑闪,一脸的新奇、羡慕表情。
的确,尽管时光以万夫不挡之势扭头向东而不再折返,但当我用记忆去打开我在儿少时用快乐串接的生活画面时,心域里就会漾起如同过年穿上碎花新衣般的幸福,而这种幸福不觉然地已成为我压箱底的财富,随便扯出一件就足以让儿子瞠目,唏嘘。
旧时年景
五谷不兴,灶门不旺的年代,弥漫贫苦的味道。
我们村巴掌大的版图上,伛背躬身的人们一边劳作,一边瑟缩在寒怆的时代背景下,承受着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困顿与煎熬。能够顿顿在饭桌前美美地捧上一碗稠饭,香香地打上串串饱嗝,成了他们最单纯,最真切的愿望。
三六九月的平常日子里,村里人家常常吃酱豆泡黄米馓饭,还有用黑面、杂面混和擀成的面条,或者拿铁锅焖煮洋芋和红薯干用于垫补饿肠瘦胃,不多的几撮雪花白面只能等到有重要亲友到家或遇到年节,才能舍得拿出来做了饭吃。即便如此,倘不能精打细算,还是会面临捉襟见肘、难以为继的境况。
当北风猎猎吹起,几场雪花肃然飘落,寒光和冷白统领着季节走向岁末。顺遂传统而来的“年”就像一树硕大艳丽的红梅,在中国大地上摇曳绽放起来,给栖居在农村这方角落的人们的眼里和心头,招摇起小小的欢愉和热情。他们抬头望“年”并在心里酝酿着美好的情愫:有布有面有油有肉过个好年!
可是,低头环顾家门里外,飘进飘出的依旧是习习寒凉和由此衍生的淡淡愁绪。因为愁眼、愁容、愁心都凝着“穷”字,所以“穷”在悄然间倒像根无形的红绳将村里人的情感紧系在一起。面对三两步之遥的“年”关,房前屋后的邻居人家相互接济,这家打发孩子去隔壁借三碗白面,那家女人来这家要两缸缸米,小年二十三,再给灶王爷磕个响头,上根高香(用柴棍当香),就能吃上漂着油花的年夜饭。冷清之中又透着暖意。
在我家,从我记事起,妈妈的眼睛总时不时地盯看面袋子的胖瘦。她扣扣掐掐,藏藏掖掖,家里的油盐酱醋米面粮,廊檐水似的嘀嗒着,倒也能凑合挨到过年,当然逢到短窄之处,妈妈也会使唤我去杨妈家、张妈家筹借。
最难以忘记的是在一个不寻常的腊月,爸爸凭着为生产队做架子车的木匠手艺,给二姨夫的朋友做了四个木凳,而姨夫的那位朋友又恰是城里饲养场的工人。所以年跟前,爸爸欣喜着从饲养场提回来一副猪下水,妈妈劲头十足地拾掇干净,那一年我家的年味终于香飘满院了。而这意外的阔气,却惹得弟弟有好几天肚子憋得哼哼叫,也不愿意上厕所,他是多么不舍得让吃进去的肉再出去呀!
那之后的好几次过年,我家就有了两幅猪下水,或者一副猪下水再加一个猪头这样流油的年。再后来姑姑姨姨这些亲戚家有零星养得起猪的,逢到那树红梅招展时,自己身上肉似的忍痛割上一溜肋条送给我家,让我们殷实一番“年”景,当然这也全仗着爸爸平时对他们有所付出。
年就是年,人们被轻愁和淡欢陪伴着,捧出心底所有的赤诚认真对待。
我家养猪了
旧“年”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又一道春风带着季节和政策变暖的消息轻轻拂来,三月的田野上,苦菜花开了,有了颜色。
村子里头脑活泛的人,搭鸡窝盖猪圈,抓猪娃养小鸡,精神抖擞起来,妈妈被养猪的心念迫使着,从邻村的姨奶奶家捉回来一头小猪,算是进入了村里养猪人的行列。
猪在圈里了,看着它扒墙拱地地闹腾,听着它“哧哧哼哼”地整日叫,妈妈心里不仅踏实,甚至还有些骄傲。凭着身后的一头猪,满盆满锅的油和肉仿佛就在眼前。
然而,日子是道长流水,噙在嘴巴里的感觉虽然没有以前那么苦涩了,但是贫寒的底味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,人们脸上的瘦皮尚未紧巴之前,哪里有更多的米面细粮来喂养一头牲畜,所以猪的日子就和人的日子一样清寡。那时,我每天放学后的头道任务便是提上篮子,去园子里,去水渠边给猪铲野菜,拔嫩草,或者到地头捡拾菜秧菜帮。回家后再略微剁碎,搅和上一把米糠或麦麸子倒进猪槽。但是,即便每天拔回家的菜菜草草堆成小山似的,终究还是青汁绿液,根本难以满足猪的肚仓,饿极了的猪就撞击着圈门整人似地嗷叫,所以我常常听妈妈对邻居说:我家“吊搭”着一头猪呢!吃不饱,就得和人一样吊着胃口吧。
长长的一年下来了,猪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些黏糊,情味就变得浓重起来。腊月开始,妈妈更勤地进到猪圈,瘦瘦长长的条子猪仿佛通着人性,嘴巴使劲拱着蹭着她的鞋底,喉咙里还“哼哼”地像是在告叨。妈妈摩挲着猪脖子上硬硬的短鬃、刀棱似的脊梁,再拍拍那松垮的猪肚皮,神情显得有些凝重,眼里也沁满怜惜。这般瘦骨嶙峋的身胚怎么能经受住宰杀呢?这样的柴猪怎么能让“年”油汪汪呢?
为了让猪圆实肥胖一些,妈妈咬牙将家里人吃的玉米面,黑面慷慨地献出来,接连着半个多月精面细料的用心喂养。临时磨刀亮三分,那猪的身子竟有些稍微得茁壮了,妈妈这才带着笑意,赶紧去约说杀猪的日子。
舅爷是屠夫
村里有四十来户人家,唯一的屠夫碰巧是我舅爷。
舅爷个头矮小,双腿向内罗圈,却能疾跑快走。在他黑幽幽的脸膛上,眉窝子时常拧成深旋,隐现一种肃杀之气。此外,他的嘴唇微微凸撅,话语极为廖少。或许正是这样的面相和神情,决定了舅爷的职业和猪联系在一起。
舅爷的家距离我家有百米至多,我上初中时,舅爷开始操刀杀猪,可能带着天性吧,舅爷杀猪有两把刷子,所以平时都有邻村操办红白事情的人家寻来,让舅爷一展身手。当时给人杀一头猪,舅爷可以挣到10---20块钱,还能落一条人家酬谢的猪尾巴。逢到年节,尤其是腊八已过,舅爷更变成村里的大匠人,凡有养猪的人家都赶着、牵着、拉着猪约请舅爷,舅爷也是磨刀霍霍,卷袖而上。
天气晴好的那天,爸爸叫来姑父准备将猪押到舅爷家去宰杀。爸爸打开圈门走进去时,那猪似乎已经感知到了它的大限来临,惊恐地躲在角落,端挺着耳朵细听四周的响动,更以钻心的嘶叫声抗拒着侵入。其实,在那几天里,村里已经不断有人将猪交付给了舅爷的屠刀。猪的嚎叫声从舅爷家的方向传出,震慑的不止是人的耳朵和心里,更有猪的同类同族。爸爸两步跨到猪的跟前,牢牢抓住猪的一只耳朵往外拽,无助的猪尖叫着两只前腿死死地抵住地面,姑父手里的柳条朝着猪的身上挥下去。
最终,惊魂不定的猪还是被绑在了架子车上。我和弟弟围在旁边,骇然若傻瓜蛋子似地看着,颤颤的心里多少也生出了些可怜,但是不消半刻,我们就蹦蹦跳跳地跟着架子车,护送般地朝向舅爷家。
惊天动地的时刻来临。歇斯底里的嚎叫声划破村子上空的凝冷,我家的猪被大人们死死地按压在木案子上,舅爷手中的短刀朝向了猪脖子下方,恐惧像一块黑布蒙住了我的心脏和眼帘。当我稍后怯怯地睁开眼时,殷红的猪血正汩汩地流向爸爸端着的面盆里,案子上躺着的猪声息全无,抽搐了几下就气血散尽,魂魄成殇。
舅爷的面目不带表情,短刀尖刃明晃一闪,猪的脚腕上便豁开一个口子。随即他俯下身子,嘴巴对着豁口,猛猛几下吹气,那猪的全身就像扁气球一样膨胀起来。这时候,大大的椭圆形的木盆里,才倒入的沸水蒸汽升腾。气鼓鼓的猪被抬放进去,翻转淹烫几下,软软的猪毛就被舅爷利利索索拔净。
接着,就像刚刚出浴一般,白胖胖的猪身子又被铁钩吊挂在木杆上。舅爷哗啦两瓢净水泼上,卷刃刮刀上下嚓嚓几声,细毛污渍哪敢停留。短刀再起,如剥葱脱衣一般,竖在我眼前的精身白肉便膛破肚开了,里面的曲曲折折暴露出来。舅爷双手深入其中,呼哧呼哧一顿掏挖,接着就听见他喊叫:脸盆子拿过来,快拿脸盆子!爸爸递过去脸盆,那些油油串串,肠肠肚肚之类的都被掬出来放置在盆子里。
就在我扑闪着眼睛看得热乎乎时,“噗嗤”一声,舅爷扔过来一团东西,“猪尿泡给你玩,你这个女子长得心疼”说话的同时,他瞅瞅我,嘴角咧咧着笑了,臊得我不好意地转过了头。
架子车载着白生生的猪肉,又在我和弟弟蹦蹦跳跳的护送下,颤颤悠悠地被推回家中。妈妈迎上来的目光带着喜悦和湿气,她已经劈好了一堆柴棒,锅里又烧上了热水。
柴灶肉香
白花花的肉就在锅台上、案板上,足足有八十斤啊!全家人的眉梢上像是都贴上了一个“喜”字,早早地将“年”接进了家门。
我和弟弟抢着抱柴、烧火,炉膛里红艳艳的火苗扑闪起来,大铁锅的水很快翻滚,妈妈将脸盆里的生猪血倒进锅里,慢慢的那些半凝固的血就紧紧地结成了大血块。妈妈说这样的血块,经过热油再炒一番别有风味。
爸爸的好脾气很难得地带动着他轻快的脚步,他耳朵软软地听从妈妈的调遣,将菜刀按在水缸边沿,“噌噌”几下磨得锃亮。接着一番技术性的切切剁剁,除了腿骨,排骨和留作丸子的花肉外,其他整块的肉都变成了小块。
一家人莺啼鸟啭似的说说笑笑,妈妈已将生的板油、水油切成小块,放入铁锅中炼制。在小火的加工下,这些油块渐渐变得金黄并且漂浮起来,等到不断有碎渣喷溅出来时,妈妈手持漏勺将这些渣粒捞出了锅。油香四溢,我和弟弟直接上手去抓吃那些油渣,都是为了将各自身体里蛰伏一年的馋虫喂饱。在那些年月里,这种油渣由于炸干了水分,随意放置许久都不生坏,所以就成了我家包饺子用的金贵馅料。
猪油炼好了,黄亮亮的装了半盆,妈妈说话的嗓子眼听起来润润的,像喝了蜜又像喝了油。铁锅里留着底油,妈妈将爸爸切好的生肉臊子倒了进去,又撒放调料、倒入酱油,不断地搅动翻炒。在艳艳的酱色之上,锅里水泡气泡小花似的开了败了,浓郁的肉香溢出来,盈满了厨房,又飘出屋外。此时,整个村庄已渐渐地没入寂静冷穆之中,几声犬叫从夜色的深浅处传来。投进灶膛里的劈柴跳动着火花,还伸吐着鲜红的小舌,我们一家人沉浸在热言暖语和肉香中,毫无疲惫和睡意。
第二天的时候,妈妈接着炸了丸子、酥肉,还煮好了下水,至于猪头和猪蹄呢,妈妈说要在房梁上挂几天,到了年三十的前一天,才拿下来放在大铁锅中烹煮。
做完这些的时候,距离过年还有七八天。 能源网 http://www.aeenets.com/
政策解读
能源人物
能源装备
亚欧能源网 广告热线:010-61224401 传真 010- 61224401
客服QQ:924467170 Email: mxzh2008@163.com Copyright
2005-2011 aeenets.com
All Rights Reserved. 亚欧能源网 版权所有 备案编号: 京ICP备12037512
本站网络实名:亚欧能源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