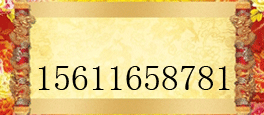不敢潇洒(随笔)
来源:中国煤炭新闻网 发布时间:2014-05-14 10:10:59
那些年我真的不敢潇洒……
我自认自己是个倒霉的男人:家虽有贤妻可因工作太忙很多 家务活不得不落在我身上;当时我虽有健在的老父老母,可他们不如别人家的能干,每天只是像去食堂那样,到时来吃饭……
我很嫉妒那些拿着茶盅,悠哉游哉,去茶馆“吹死牛”、侃大山,或是围在桌前,玩纸牌、砌“长城”的男人们。他们不用忙于油盐柴米,也不用去菜市讨价还价,这些都是女人活,男人嘛,就得像个男人。可我这个倒霉的男人,偏偏摊上女人之活。
其实,我也想潇洒,只是不敢潇洒。妻在上班,家里没菜,能不去买吗?儿子上学,老父老母到时要来吃饭,家里有没人做,我是躲也躲不过,推也推不掉,只好放下大男人架子,硬着头皮,做起女人活……
相当初,我是何等悠闲,何等的潇洒。闲时几个狐朋狗友,攒在一起,“吹死牛”,“冲壳子” 。要么提两瓶老白干,切一盘脆耳朵,称一些花生米,喝酒划拳,吟诗作对,要多狂,有多狂,要多颠,有多颠,反正喝酒吹牛都不上税,来个通宵达旦。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我开门一看,不好,是妻找来了,她委屈地流着泪问:“你为什么不回家?……”
一次铁哥们过生日,我们疯狂得最带劲时,妻又打着电筒找来:儿子在家发高烧!我只好恋恋不舍地向哥儿们,说了声对不起……
还有一次更荒唐,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,我带着儿子去荒郊野外的河堰游泳。回家路上哥儿们一片诚意,摆开酒宴。我们虽说是狐朋狗友,但也有雅兴,在酒桌上,谈唐诗,论宋词,谈到投入处,也效仿古人,酒到兴头,诗兴大发, 一个哥们对着墙上的一副风景画,来了几句:
松旁溪水脚下云,远山夕阳拂金辉,
蓬莱仙景岂可比,名山圣境天下闻。
接着又一个哥们更赋诗唱和:
松绕白云闻溪鸣,遥遥天际金染成,
微风才动云翻涌,人间仙境此山寻。
大家你一杯,我一杯,围绕着两首激情创作诗,大发感慨,接着又谈古今,论国事,说天南海北。一瓶喝完了,又提二瓶,二瓶扯光了,又来第三瓶……不知不觉已是夜里十一点过了,儿子在一旁直吵要回家,没法,只得余兴未尽,就此打住。
殊不知,在我最兴奋,最颠狂的时刻,就是妻最着急,最担心的时候。丈夫下午就带着儿子去游泳,天黑了,还不见归来,哪个妻子不着急,哪个母亲不担心。妻慌得像热锅里的蚂蚁,四处打听,凡是当天下午去过河堰游泳的人,她都问遍了,后来妻子挨家挨户地找到我平时要好的朋友们,仍没着落,妻流着伤心的泪水,打着电筒,独自找到离家几公里外的河堰来, 还好,在半路上就碰上了我们几个酒疯子,妻不安的心总算平静了,但她的不满后来愈来愈明显。
从那后,我每次出门,妻都会脚跟脚地找来,有时弄得我非常尴尬。妻还常教导我说:“你是有家小的人……”
为了孝敬年迈的父母,为了全家人的生计,为了家庭的和睦温馨,为了儿子健康成长,我宁愿舍去那份闲情与潇洒。
作者:川煤威达公司退管委 张承捷能源网 http://www.aeenets.com/
我自认自己是个倒霉的男人:家虽有贤妻可因工作太忙很多 家务活不得不落在我身上;当时我虽有健在的老父老母,可他们不如别人家的能干,每天只是像去食堂那样,到时来吃饭……
我很嫉妒那些拿着茶盅,悠哉游哉,去茶馆“吹死牛”、侃大山,或是围在桌前,玩纸牌、砌“长城”的男人们。他们不用忙于油盐柴米,也不用去菜市讨价还价,这些都是女人活,男人嘛,就得像个男人。可我这个倒霉的男人,偏偏摊上女人之活。
其实,我也想潇洒,只是不敢潇洒。妻在上班,家里没菜,能不去买吗?儿子上学,老父老母到时要来吃饭,家里有没人做,我是躲也躲不过,推也推不掉,只好放下大男人架子,硬着头皮,做起女人活……
相当初,我是何等悠闲,何等的潇洒。闲时几个狐朋狗友,攒在一起,“吹死牛”,“冲壳子” 。要么提两瓶老白干,切一盘脆耳朵,称一些花生米,喝酒划拳,吟诗作对,要多狂,有多狂,要多颠,有多颠,反正喝酒吹牛都不上税,来个通宵达旦。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我开门一看,不好,是妻找来了,她委屈地流着泪问:“你为什么不回家?……”
一次铁哥们过生日,我们疯狂得最带劲时,妻又打着电筒找来:儿子在家发高烧!我只好恋恋不舍地向哥儿们,说了声对不起……
还有一次更荒唐,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,我带着儿子去荒郊野外的河堰游泳。回家路上哥儿们一片诚意,摆开酒宴。我们虽说是狐朋狗友,但也有雅兴,在酒桌上,谈唐诗,论宋词,谈到投入处,也效仿古人,酒到兴头,诗兴大发, 一个哥们对着墙上的一副风景画,来了几句:
松旁溪水脚下云,远山夕阳拂金辉,
蓬莱仙景岂可比,名山圣境天下闻。
接着又一个哥们更赋诗唱和:
松绕白云闻溪鸣,遥遥天际金染成,
微风才动云翻涌,人间仙境此山寻。
大家你一杯,我一杯,围绕着两首激情创作诗,大发感慨,接着又谈古今,论国事,说天南海北。一瓶喝完了,又提二瓶,二瓶扯光了,又来第三瓶……不知不觉已是夜里十一点过了,儿子在一旁直吵要回家,没法,只得余兴未尽,就此打住。
殊不知,在我最兴奋,最颠狂的时刻,就是妻最着急,最担心的时候。丈夫下午就带着儿子去游泳,天黑了,还不见归来,哪个妻子不着急,哪个母亲不担心。妻慌得像热锅里的蚂蚁,四处打听,凡是当天下午去过河堰游泳的人,她都问遍了,后来妻子挨家挨户地找到我平时要好的朋友们,仍没着落,妻流着伤心的泪水,打着电筒,独自找到离家几公里外的河堰来, 还好,在半路上就碰上了我们几个酒疯子,妻不安的心总算平静了,但她的不满后来愈来愈明显。
从那后,我每次出门,妻都会脚跟脚地找来,有时弄得我非常尴尬。妻还常教导我说:“你是有家小的人……”
一次,妻和我还有我几个铁哥们,一起去游玩,哥儿们特买好酒好菜,要款待我们夫妇,可妻不领情,也不许我去,结果把我的狐朋狗友全得罪了。回家后,我们大闹一场,输方,自然是我,哥儿们不再来找我了,我只好憋在家里听妻的话:我是有家小的人,再后来父母又从边远矿区迁来了,他们都是七十七八岁的高龄,我还指望他们帮什么忙?只要他们不生病,不上医院,也就万幸了。儿子进入中学后,他的学习压力,不比我上班轻松,我还得为他提供条件才是。紧接着妻单位倒闭,妻下了岗,我不得不为全家的出路操心啊……
为了孝敬年迈的父母,为了全家人的生计,为了家庭的和睦温馨,为了儿子健康成长,我宁愿舍去那份闲情与潇洒。
作者:川煤威达公司退管委 张承捷能源网 http://www.aeenets.com/
政策解读
能源人物
能源装备
亚欧能源网 广告热线:010-61224401 传真 010- 61224401
客服QQ:924467170 Email: mxzh2008@163.com Copyright
2005-2011 aeenets.com
All Rights Reserved. 亚欧能源网 版权所有 备案编号: 京ICP备12037512
本站网络实名:亚欧能源网